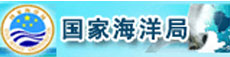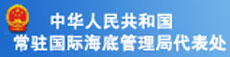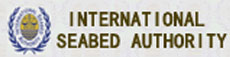科技日報:西南印度洋,這里的熱液生物不一般
發布日期:2018-06-19 17:24:30
寒冷、高壓、低氧、沒有光照、營養物質匱乏……在黑暗廣袤的深海海底,在零星分布的高溫熱液噴涌的極端環境中,卻出現了生機勃勃的“綠洲”。
自1977年“阿爾文”號深潛器發現深海熱液噴口生態系統以來,熱液生物逐漸進入人們視野,并成為國際海洋研究的熱點和前沿領域。可是,在全球熱液生物地理分布的版圖上,卻有很多“模糊的拼圖”。印度洋就是其一,其認知程度明顯較低。
近日,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王春生研究員領導的課題組在國際學術期刊《深海研究》(Deep-Sea Research Part I)以封面文章的形式發表了一篇論文,系統地闡述和總結了西南印度洋熱液生物的物種組成和多樣性特征,為拼接全球熱液生物地理版圖提供進一步證據。
作為該研究的第一作者,大洋49航次第四航段生物組組長周亞東向科技日報記者透露,目前已記錄西南印度洋熱液區巨型底棲動物物種39種;18種為該區的第一次報道,有一半種類尚未正式命名;,“這也是目前對超慢速擴張洋脊熱液生物群落年際變化的首次報道” 。
顛覆“萬物生長靠太陽”
在周亞東看來,如果說通常意義上的陸地和水生生態系統是太陽能驅動,那么熱液生態系統則是靠“地熱能”驅動。地球深部的能量經過一系列復雜的物理、化學反應,最后經過微生物的“固定”而進入海洋底棲動物的食物鏈,并支撐形成這個小而精密,且快速演變的系統。
雖然生存壓力巨大,但熱液噴口周圍聚集生長了豐富的生物類群。“熱液生物呈現高豐度和高生產力,目前人類發現的熱液生物已達700余種,平均每個月就發現兩個新種。”周亞東說,熱液區中熱液生物密度非常之高,遠超出一般海洋生態系統,一升海水的盲蝦數量最高可達上千只。
“但這種繁榮是短暫的,熱液生物群落對于噴口活動高度依賴。熱液噴口壽命有限,有的只活動幾十年,極端的情況如東太平洋海隆一次火山爆發后,熱液噴口生物群落從形成到成熟再到消亡有時只需十年左右。” 周亞東說
印度洋中脊熱液生物認知程度較低
周亞東向記者展示了全球已發現的70余處發育有典型生物群落的熱液區,主要分布于太平洋周邊和北大西洋,印度洋其次,南大洋有少量發現,北極圈內雖有熱液區但還沒有發現典型的熱液生物。
熱液生物區域特征顯著,“不同海區的熱液噴口生物群落的外觀和物種組成有明顯的差別,形成獨特的地方特色,如東太平洋海隆特有的、最長可達3米的巨型管棲蠕蟲。”周亞東說,科學家據此對全球熱液生物群落進行地理分區。這有點類似行政區的劃分,按照生物組成,全球熱液生物群落最多可被分成東太平洋海隆(南段)、東太平洋海隆(北段)、印度洋、南大洋等11個獨立的“生物省”。
印度洋中脊是現存連接太平洋洋脊系統和大西洋洋脊的唯一洋脊,因此學者普遍推測,它是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熱液生物的現存唯一通道,驗證這一假說成為印度洋熱液生物調查和研究的主要驅動力之一。
首次揭秘三大熱液區的“黑暗生物圈”
這篇論文主要基于中國大洋科學考察2014-2015年兩個航次的積累,描述了西南印度洋“龍旂”、“斷橋”和“天成”3個熱液生物群落,其中“斷橋”和“天成”為首次描述。
往往一個海區的生物相似性較高,但西南印度洋南北熱液區之間物種組成差異較大,以優勢種而言,“天成”以印度洋深海偏頂蛤和甲胄海葵為優勢種;“龍旂”則以宙斯盾巨佩托螺、茗荷為優勢種。
如果我們把印度洋當成一個生物省,那么,西南印度洋和中印度洋則相當于兩個地級市。而西南印度洋北部的“天成”熱液區與中印度洋更接近,應該屬于“中印度洋市”;南部的“龍旂”和“斷橋”熱液區雖總體仍與中印度洋最接近,但兼具北大西洋脊、東斯科舍脊和中印度洋熱液區的部分特征,明顯受到來自這三個區的影響,其物種組成顯得更加多元。“這說明生物的相似性與地理位置基本吻合。” 周亞東說,“龍旂”和“斷橋”可能是上述三個洋脊之間的過渡區。“這使我們對印度洋熱液生物區系的劃分有更細致深入的認識。”
與2011年相比,2015年“龍旂”的噴口活動狀態以及生物群落結構總體穩定,但仍發現極個別煙囪體的噴發減弱并伴隨生物群落的劇烈變化。如1號煙囪體上,在2015年,一些“高溫種”消失,同時一些“低溫種”卻大量出現,如貽貝和茗荷。“這一變化很可能與熱液活動強度的顯著衰減有關。”
正在西南印度洋執行大洋49航次的科考隊員剛剛結束第四航段任務,調查隊雖沒發現熱液生物,但第一航段應用電視抓斗在“天成”熱液區僅發現少量的海葵和腹足類,如果這與論文里報道的群落是同一個位置,這表明天成熱液區可能已經處于演替末期。
周亞東透露,下一步研究人員將加快物種鑒定和命名,取得該區域完整的熱液生物名錄,同時加強部分熱液區調查力度,關注其年際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