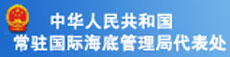碧海長灘書錦繡——自然資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保護地管理和生態化建設研究紀實
發布日期:2020-04-13 09:10:03



科研團隊在黃河口開展海上調查。

科研團隊參加東亞海國際會議。

科研團隊開展江蘇灘涂現場調查
海岸線是海洋經濟發展的生命線、黃金線,具有重要的生態功能和資源價值。中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和豐富的海岸帶資源,海岸帶匯聚著河口、海灣、濕地等重要的生態系統,保護責任重大。
在自然資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就有這樣一支由70后、80后和90后組成的科研團隊,他們致力于海洋保護地的管理和生態化建設研究,長期奮戰在祖國的碧海長灘,他們在這里撒下了青春與汗水,也收獲了希望與未來。
筑夢黃河口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從青藏高原奔流九省后于山東東營入海,所形成的廣闊流域和肥沃土地孕育了偉大的中華文明。由于黃河攜帶的大量泥沙和營養物質進入海洋,使黃河口成為許多海洋生物與鳥類的棲息地、產卵地和索餌育幼場。
2005年初秋,正在開展《東營市海岸帶綜合管理規劃》調研的張朝暉博士來到黃河口。無際的蘆葦蕩,靜謐流淌的黃河悠然地匯入大海,猶如一位慈祥的母親,默默地滋養著這片土地上的生靈。張朝暉說,自己被這壯麗的大自然深深征服,當時就樹立了一個堅定的信念:這里的自然生態就是這片土地的靈魂,一定要保護好才行。
隨著工作的深入,張朝暉對生長在黃河口的人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1983年建市的東營曾是土地鹽堿化非常嚴重的地方,被列為綠化禁區,更被笑稱“東營的電線桿比樹多,在東營種活一棵樹比養大個娃還難!”可東營人硬是讓成片樹木在這里扎根繁茂。這種執著、踏實、肯干的精神也激勵著時年35歲的張朝暉,他的心在黃河口扎下了根。
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災害的管理是海岸帶綜合管理的三大基石,如何讓科學研究更好地為海岸帶綜合管理提供支撐一直是縈繞在張朝暉心頭的一件大事。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在東營市的支持下,張朝暉帶領著團隊開始了對黃河口區域的調查研究,并將獲得的資料和數據應用于東營市環境治理、資源管理和生態修復決策中。2010年,他與多家單位聯合申報的海洋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黃河口及鄰近海域生態系統管理關鍵技術研究及應用”成功立項。
在此后4年的研究中,張朝暉又發現了新問題,黃河口及其周邊海域的生態環境和資源狀況與上游來水量密切相關,可僅有的幾年數據無法找到生態相關性在哪里,更無法知道怎樣能改善生態環境和資源狀況。張朝暉心有不甘,于是他再一次開啟了求助之路,與黃河水利委員會、中國海洋大學以及東營市相關單位等進行合作或搭載航次開展調查研究,一直堅持到了今天。
隨著數據的增多,生態學關系也逐漸顯現。團隊發現黃河口生物資源的補充量對春季入海淡水有重大需求,并最終得出了3~5月份黃河入海徑流量不低于26.8億立方米以及全年不低于200億立方米的兩個生態需水紅線,為陸海統籌聯動治理黃河流域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黃河委也據此實施了水資源生態調度,加大了春季入海淡水量,改善生態首次成為民生要素以外的決策考量。最新監測結果顯示,2019年魚卵仔魚密度比2009年增加3~10倍,黃河口產卵場功能正在恢復,海草床、牡蠣礁等也在黃河口重現,黃河口海域正恢復著往日的生機。
重現海岸帶昔日風采
黃河口有河有海,既擁有著生機盎然的濱海濕地和生態保護地,也存在養殖和油氣開采活動。豐富的資源要素和復雜的生態系統構成,對科研工作既是財富又是挑戰。隨著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加入,一支涵蓋海洋生物學、生態學、環境科學、海洋化學、海洋遙感、管理學等多學科科研團隊成長起來。該團隊以黃河三角洲為依托,專門從事海洋保護地管理和生態化建設研究,長年活躍在祖國的碧海長灘。
“黃河口的風浪令我終生難忘!”這是海洋一所助理研究員趙林林博士最真實的感受。在黃河口出海調查時,海上濕冷的風可以刺破任何防護服,凍得骨頭發疼。趙林林說,這還不算最難受的,海上風大時,租來的漁船像是飄零的落葉,在海上顛簸搖晃,硬是把不暈船的他給晃吐了。
“和風浪引起的不適比起來,船上簡單的伙食和極差的衛生條件都不算什么困難了。”趙林林笑著說。
一年出海4次,一次外業十多天,60多個站點,趙林林就這樣一點點地從大海里“撈數據”。十年過去了,趙林林已經從一個26歲的小伙子成長為團隊主力,帶領著海洋保護地科研組開展各項研究。
海洋保護地在我國建設時間短,缺乏科研基礎。團隊先后探索研究出了多種技術,包括海洋生態重要區識別技術和系統保護規劃法相結合的選劃技術、基于環境DNA和分子標志的保護對象監測技術、重要保護對象的恢復保育技術、基于聚集度和威脅度的保護對象評估技術和海洋保護地管理成效評估方法等,為遼寧、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和海南三沙市的海洋保護地建設和管理提供技術支持。如今團隊又融入到“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改革中。
對受損區域進行生態恢復也是保護的重要內容。2012年博士畢業后,王煒便一頭扎進了黃河三角洲的鹽堿灘,從檉柳和堿蓬等典型工具物種入手,研究鹽堿灘恢復模式和應用場景,并逐漸摸清了我國海岸帶檉柳和堿蓬的種類、分布、生物和生態學特征,掌握了修復技術。他的成果為“南紅北柳”重點生態工程提供了有力支撐,針對一些地方修復中出現“為種而種”的誤區,他反復和地方同志溝通強調“濱海濕地修復是生態工程,而不僅僅是種植工程,應重點關注生態功能的恢復”,如今這一理念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一線管理人員認可。
生態恢復工程研究和實踐往往是不斷試錯的艱難過程。為了在東營的灘涂上恢復堿蓬,王煒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潮水太大,剛播下的種子被沖跑,潮水太小,剛冒頭的堿蓬被干死。王煒記不清自己究竟試驗了多少次,鹽堿地上的風吹日曬已經成為家常便飯。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終于,他掌握了潮汐規律和堿蓬恢復關鍵,不僅成功令紅地毯在退化區重現,還吸引了反嘴鷸等鳥類來此下蛋,黃河口濱海濕地的鳥類棲息地功能日漸恢復。
江蘇如東縣的灘涂濕地是國際上的重要候鳥遷徙中轉站,但是受外來物種互花米草的影響,鳥類棲息地的生態功能受到嚴重破壞。當地政府也曾組織清理互花米草,但是收效甚微。如何找到一個切實可行的治理方式成為當地政府多年的困擾,后來,這個問題轉到了海洋保護地管理和生態化建設研究團隊手里。
從青島去如東開車單程一趟7個小時,王煒和同事們這一跑就是3年。功夫不負有心人,團隊利用物理和生物方法結合,最終提出“海泥掩埋+物種替代”的綜合防治方案,并借助附近港汊整治的契機,通過精確的高程測量,嚴格控制掩埋深度。一方面清理米草,另一方面保證灘涂的潮間帶屬性,同時用堿蓬、蘆葦等原生植物替代米草。如今,勺嘴鷸等瀕危鳥類又重新出現在項目區。監測結果顯示,修復區的鳥類種類數是對照區的3倍,數量是對照區的140多倍。而隨著修復工作的逐步推進,如東這一黃海重要濱海鳥類通道和棲息地生態功能恢復指日可待。
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理念不斷增強,政府和公眾也意識到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如果說樸素的保護意識是當年站在黃河入海口前張朝暉博士心中的點點星火,如今它已經成了燎原之勢,成為整個科研團隊核心,照亮了他們前行的路。
推動海洋國際合作見實效
如不是親眼所見,很難將這些整日與海水泥灘打交道的人和洋氣的國際合作聯系在一起。他們時而赤腳走在泥灘上,轉身又西裝革履地出現在國際會議上,為更廣泛的海洋保護努力著。
“國際合作高投入、慢產出,對人的綜合素質要求極高,既要專業過硬、英語好,還要有大局觀。所以很多人做不了、不愿做,科研機構也無法將它納入考核指標,導致從事國際合作的科研人員嚴重缺乏。”張朝暉感嘆道,“海洋是聯通的,是典型的生命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無論是從科學本身的發展,還是國家的海洋強國戰略實施,都離不開國際交流合作,我們既要吸取國外的先進經驗,還要將我們好的理念、經驗和實踐成果推廣出去,共同推動海洋保護和管理。”
2010年,張朝暉團隊在實施東亞海環境管理伙伴關系組織(PEMSEA)第三期項目時需要編制《海岸帶狀況報告》,當時外方專家要求中國采用他們制訂的160個指標,可其中大部分指標不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張朝暉帶著團隊一起研究了國際上全部案例,然后根據中國的需求,經過十幾稿的完善,最終提出了27個核心指標加5個選用指標的方案。可此方案一經提出便遭到了外方專家的強烈反對,此后他們與外方專家進行了長達半年多的激烈爭論,討論持續從國內到國外,從網絡郵件到會場,最終外方專家接受了團隊的觀點,將此方案應用到22個中國海岸帶綜合管理示范區。“一個不能實事求是的海岸帶狀況報告對中國沒有任何意義,我們是要解決問題,不是制造問題。”張朝暉說。
張朝暉團隊長期保持著務實作風,創造了很多優秀經驗并分享給國際社會。在1993年開始的PEMSEA項目中,中國一直是海岸帶綜合管理的經驗引進國,但到2013年時,中國已經成為了經驗輸出國。最近出版的《東亞海區域海岸帶綜合管理最佳實踐》一書,其中共梳理了12個成員國的47個成功案例,其中14個案例來自中國。2014年底,原國家海洋局和PEMSEA在海洋一所設立了中國-PEMSEA海岸帶可持續管理合作中心,以更好地推動《東亞海可持續發展戰略》和東亞海第四期項目在中國的順利實施。
相比PEMSEA的有花有果,全球環境基金(GEF)/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中國典型河口生物多樣性保護恢復和保護地網絡化項目的一波三折,則讓海洋一所的科研團隊真正體會到推動國際合作的艱辛。
“項目從2009年開始策劃,到2012年正式獲得GEF的批準,此前一切進展順利,但自此之后卻變得困難重重。”一直帶著國際合作組全程參與到項目策劃和申報的海洋一所工程師王守強說,“與FAO的執行協議內容一直討論到2017年才正式簽署,由于此項目在黃河口和珠江口的12個保護地實施,最終于2019年初根據機構改革確定了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為項目中方主管單位。”
正當眾人都期待著項目如期啟動時,FAO高層卻要求將項目主管單位再改回自然資源部,這意味著要重新修改項目執行協議,項目還將無限期延遲。負責此項目的海洋一所副研究員叢柏林博士聽到消息后急得一夜無眠。這是他加入團隊后承擔的第一個項目,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項目轉到國家林草局后也受到了高度重視,如果繼續拖下去,GEF很可能取消河口項目。“這不是丟自己的臉,而是丟國家的臉。”第二天早上,叢柏林紅著眼睛把一夜的思考寫成英文郵件直接發到了聯合國糧農組織總部,里面明確指出:“一旦項目被取消,FAO必須承擔全部責任。”幾天后FAO總部回函稱:他們認同叢柏林的觀點,不修改項目執行協議,經過綜合評估后仍然由國家林草局來組織實施。
2020年初,河口項目國家管理辦公室正式落戶在海洋一所。海洋一所的科研團隊為什么對這個項目如此堅守呢?
“中國的海洋保護地面積都相對較小,如何實現保護效益的最大化始終是科研界的一個難題。”張朝暉說,“通過河口項目的實施,我們可以驗證‘保護地網絡化’這一理念在中國的實施效果,摸索出自己的經驗,從保護地間的生態關聯性入手,探索我國近岸海洋保護地的協同管理。”
構筑人才建設新優勢
海洋保護地管理和生態化建設研究團隊尤其重視青年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在這個23人的團隊中,僅有5個70后,其他都是80后和90后。這些年輕科學家的研究方向和科研發展得到了優先保障。
2018年機構改革后,海洋保護地管理從原國家海洋局轉移到國家林草局,為了摸清海洋保護地的情況,盡快開展工作,國家林草局提出向海洋一所借調專家,以協助機構改革期間業務的交接和工作開展。憑借優秀的理論基礎、一線工作實踐積累,80后趙林林被推薦到國家林草局協助工作,其優秀的工作表現獲得了充分肯定。
90后朱曉彤加入團隊時剛剛畢業,為了讓年輕人快速成長,團隊將她派至菲律賓的PEMSEA秘書處實習。同時,海洋一所國際合作處適時出臺了相關的管理辦法,為年輕科研人員的發展提供政策保障。現在,朱曉彤已經成為了海洋國際合作的行家里手,專業翻譯嫻熟自如。
除了加強內部人才培養,團隊也高度重視對各海洋保護地管理人才的培養。自2014年開始,主動承擔起了全國海洋保護地的培訓工作,在各相關主管部門的支持下,該培訓已經舉辦了5期,先后有600多名來自一線的海洋保護地管理和技術人員接受了培訓。通過培訓不僅顯著地提升了海洋保護地管理者的業務水平,還為科研工作者、保護地管理者、地方管理人員和業務主管部門搭建了一個溝通的平臺,得到了學員們的歡迎和認可。
近年來,海洋保護地管理和生態化建設研究團隊在海洋保護地選劃、資源調查、生態修復和生態保護相關基礎研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技術,特別是在海洋一所“拓海探極”的發展思路指引下,團隊已將海洋保護工作拓展到了極地和大洋。雖然始于碧海長灘,但團隊卻利用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到公海保護區選劃、遠海資源評價等工作中,積極為中國參與全球海洋治理作出新的貢獻。
因為熱愛海洋保護,喜歡探索研究,海洋保護地管理和生態化建設研究團隊十幾年如一日,憑著共同的理想和目標,潛心把解決實際問題作為研究主導目標,搭建起了科研為管理服務的橋梁。
2018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優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績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此后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聯合發布了《關于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國家對自然保護地和對專業人才培養的重視讓團隊更加堅定了前進的方向,作為一支應用型科研隊伍,我們期待著通過自己的努力將中國建設成海洋強國,期待著能在祖國的碧海長灘上做出更多錦繡文章。”張朝暉說。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10270號 地址: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1號 郵編:100860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10270號 地址: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1號 郵編:100860